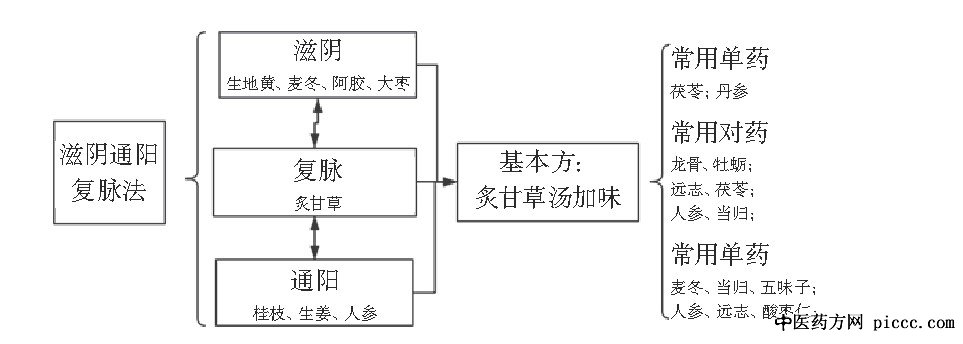|
从肠道微生态看中医肾病学的发展机
《文子·上义》载:“苟利于民, 不必法古;苟周于事, 不必循俗”。中华历史上下5 000年, 文明之舟从暗夜驶来, 正因为中医药的发展、传承、护佑, 才未倾覆浊流。然而正如中国的先人们早在2 500多年前就认识到的, 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一切科学的灵魂所在。我国微生态学奠墓人、微生物学界泰斗之一魏曦教授生前曾有著名观点:“微生态学很可能是打开中医奥秘大门的一把金钥匙”[1]。30年前的一句论断, 如久远的一束光, 已照进了如今的现实中。人体微生态与健康和疾病研究正在引发生命科学、医学、药学、机械、信息等领域的重大变革[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于2016年12月25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并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是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 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保护人民健康制定的办法。历经数千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检验, 可以说中医药的疗效、地位和作用, 已是一种“已知”, 但中医药学的一些重要内容, 如证候、药物起效机制、作用靶点的客观证据和生物学基础等, 仍需要寻找研究突破口, 今天有望在微生态学中找到答案。
“肾为先天之本”, 中医肾病学在中医内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肾脏病因其攀升的流行率[3]、巨大的社会和卫生经济负担亦寻求中医药一体化治疗的介入。藉此背景, 本文将概述肠道微生态学与中医肾脏病研究的关联和重要意义, 并探求肠道微生态作为人体微生态的最重要组成, 其能否作为一座通往“已知”的桥梁, 更新对中医药科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 谋求经由肠道微生态学之“桥梁”, 找到对疾病的干预和改善途径, 愈加明确“桥梁”所通往的方向, 从肠道微生态角度, 理解中医肾病学的挑战和机遇。
肠道菌群微生态与肾脏病关系概述
“微生态学”这一概念最早在1977年被首次提出[4], 人体微生态即是指以人体为宿主, 存在人体内与之共生的微生物群的总和, 并在近年来的主流研究中以“被遗忘的新器官”、人体的“第二个基因组”等角色被重新认识[5,6]。人体内的微生态系统共分为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及皮肤四大体系, 其中胃肠道 (gut) 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和排泄器官, 不仅是一个与各系统均有对话反馈机制的活跃器官, 也是微生物与宿主相互作用的最主要场所[4]。其作为宿主 (人体) 最重要、最复杂的微生态系统组成部分及微生物群落最主要的栖息地, 多达100万亿以上15 000~36 000个菌种的细菌构成一个巨大的微生物群落寄生其间[7], 这些肠道菌群 (gut microbiota) 构成“肠道微生态系统 (intestinal micro-ecogical system) ”。
慢性肾脏病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患者肾脏和胃肠道 (GI) 之间存在密切、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即“肾-肠轴 (kidney-gut axis) ”学说, 于2011年被Meijers B K等[8]首次提出;2015年, Pahl M V等[9]又提出“慢性肾脏病-结肠轴 (chronic kidney diseasecolonic axis) ”概念;其核心观点均着重强调以肠为中心的改变, 如肠道菌群紊乱和肠屏障结构及功能的破坏等在CKD进展中所扮演的核心作用, 其可能通过引发慢性炎症、增加心血管风险、加重尿毒症毒素蓄积等途径在CKD患者中造成系统性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肠道菌群即“肠黏膜生物屏障”, 作为CKD中“肾-肠轴”的中心环节, 其结构功能改变可能参与了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进展[10,11]。“CKD进展微生态中心论”提出肠道菌群由CKD初始阶段的适应性改变转为CKD晚期的适应不良, 导致并加剧了CKD进展和并发症的发生[12]。
肾脏病与肠道微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1.终末期肾病 (ESRD) 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
肠源性尿毒素蓄积:在尿毒症状态下, 对于肾功能减退的CKD患者, 本来应该由肾脏排泄代谢的废物如氮质毒素等, 不能充分经肾脏排泄而蓄积于体内——根据分子大小、理化性质等, 尿毒素可大致分为3类[13,14,15,16], 首先是:水溶性、不与蛋白结合的小分子物质, 如尿素氮和肌酐等, 可被血液透析所清除;其次是中分子毒素, 如甲状旁腺素和β2微球蛋白, 腹膜透析对其的清除能力较传统血液透析为佳;第三蛋白结合性尿毒素, 如硫酸对甲酚 (p-cresol) 、硫酸吲哚酚 (indoxyl-sulfate) 以及三甲胺氧化物 (trimethylamine-N-oxide, TMAO) 等。其中, 蛋白结合性尿毒素即“肠源性尿毒素”, 来源于食物并由肠道菌群发酵, 称之为“肠源性毒素”;此类毒素, 不仅难于被透析清除, 且能够刺激氧化应激, 反过来又加剧了心血管疾病进展和冠状动脉疾病的发生[9,13,14,15]。
肠道菌群紊乱:尿毒素在血液中蓄积而不能被受损的肾脏及时清除, 导致血液中的废物浓度升高继而通过丰富的肠壁血管进入肠腔使肠腔内呈现高代谢废物水平状态, 最终使肠道菌群的结构、数量和分布发生显著的改变也即导致肠道微生态严重失衡, 可表现为肠道上皮大量分泌的尿酸和草酸, 益生菌减少, 腐生菌过度生长, 且出现大量机会/条件致病菌, 改变肠道生化环境, 使相对无菌的小肠呈现出与结肠相似的菌群结构[17], 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快肾功能减退。
肠道菌群失调与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受损:肠道上皮发挥着重要的屏障功能, 可防止细菌、内毒素、抗原等进入机体内环境。有研究[6,10]表明, CKD患者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往往会遭到破坏, 通透性病理性增加而成为“渗漏性肠道 (leaky gut) ”。最近的研究[18]发现肠道菌群失调, 以及肠通透性增高和脂多糖的高循环水平, 即“内毒素血症”是CKD和ESRD透析患者的共通特征。肠源性尿毒素和条件致病菌经渗漏肠道而进入血液循环, 诱导全身性微炎性反应。故而接受维持性透析的ESRD患者, 正如前所述, 除菌群变化之外, 其肠道上皮组织亦会出现例如炎性细胞浸润肠道固有层、绒毛高度降低、隐窝延伸等类慢性结肠炎病理改变;并且此变化与血液肠源性细菌DNA高度相关。
2.肠道微生态在慢性肾功能衰竭 (chronic renal failure, CRF) 中对肾脏的影响
在CRF患者中, 心血管疾病是最常见的死因[19], 诸多可增高心血管病病死率, 如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均是CRF的传统风险因素。而炎性反应状态, 包括慢性炎性反应、微炎性反应, 作为非常规的危险因素, 不仅可以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 同时也是CKD中心血管病的重要催化剂。新近研究揭示罹患CKD后患者肠道微生态发生深刻改变;其中两个重要的病理生理学概念解释肠道微菌群对肾脏的作用关系[10]: (1) 来源于胃肠道中蛋白质和其他含氮物质在经细菌发酵累积后导致有毒终产物产生和积累; (2) 由于肠上皮屏障损害与尿毒症环境下肠道微生物的数量/性质改变, 所产生的大量内毒素甚至活菌由肠腔移位入血;即使在没有临床显性感染的情况下, 此过程仍会触发或加重ESRD特征性的炎性反应状态;如暴露于来自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的脂多糖成分等会产生由先天免疫应答所致的炎性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 这些以胃肠道为中心的改变足以触发慢性炎性反应, 增加心血管风险和恶化尿毒症, 从而可能在CRF患者中造成相关的系统性后果。指向了CKD-CRF进程中肠道微生态组成的改变可能导致肠源性尿毒症毒素的积累和系统性炎性反应, 其在加重心血管疾病和许多其它CKD相关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中起中心作用。
从肠道微生态看中医肾病学的发展机遇
1.中医理论的再发挥——“脾肾观”与肠道微生态
肠道是中医脾胃实现功能的主要部位。《素问·五藏生成》指出:“肾之合也, 其荣发也, 其主脾也”。纵览有关脾肾关系生理、病理的经典著述, 站在今时今日的理论系统与时空之下, 我们应进一步认识脾胃与肾脏间关系。
“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的理论发源于《黄帝内经》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谷气通于脾, 六经为川, 肠胃为海, 九窍为水注之气, 九窍者, 五脏主之。五脏皆得胃气, 乃能通利”、“人以脾胃为本, 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等著名理论, 是为“脾胃学说”创始人,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著名医家李杲的核心学术思想。明代李中梓有关脾肾两脏的论述“肾为先天之本, 脾为后天之本”至今仍被奉为圭臬。清代吴谦等《医宗金鉴》亦有云:“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 则生生而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 始化化而不穷也”。脾胃乃“水谷之海”, 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肾为先天之本, 脾胃健运方能以后天养先天, 并与机体的免疫功能和营养状况密切相关。早年间有学者即对中医“脾”与消化道正常菌群的关系进行总结[20], 认为脾主运化水谷精微、脾开窍于口, 能知五谷;指出中医“脾”与消化道正常菌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中医学理论认为, “脾肾亏虚、浊毒内蕴”是CRF乃至尿毒症的基本病机。CRF以浊邪壅塞三焦为标, 脾肾正气虚衰为本, 中焦气机升降失常, 则肾失开合, 水湿不运, 浊毒内生, 蕴积中焦, 内外不通, 脏腑功能失调, 体内氮质及其代谢产物不能正常排泄, 阻碍胃气之和降;或日久则气机不畅, 瘀浊互结, 而呈邪实留恋之势。正如《内伤集要》曰:“胃为肾关门, 肾衰胃不能司开合, 胃无约束, 任其越出”。“脾主为卫”出自《灵枢·五癃津液别》, 其传统理论机制是:脾胃运化功能正常, 正气充盛, 邪不外侵, 卫气化源充足, 卫外有权。近年国内有学者从抵御外邪、驱邪外出甚则肠道黏膜免疫等方面研究“脾之为卫”的内涵与外延[21], 此理论对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关系及防治具有重要指导和启迪意义。国内外又有大量数据表明肠道微生态的改善能有效地改善肾功能, 从脾-肠-肾的联系这一角度看, 也就为补脾整肠而益肾找到了更充分的理由[21]。
2.重新认识中医肾病相关证候
证候, 是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的综合概括, 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中心环节, 也是疾病病理变化的本质所在[22,23];围绕证候本质的研究亦是近年中医现代化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 但在揭示其科学内涵、解释与现代医学疾病诊断关系的道路上仍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如有学者所说, “我们可以通过某块土地上的植被种类与生长状态来推测土壤的基本特性”[24], 肠道微生态以其与中医“整体观”“系统观”“恒动观”“平衡观”等共通的特点[25], 同时可作为证候客观指标化的延伸, 为疾病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客观化整体指标。
目前有关中医证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脾虚证、肾阳虚衰证、湿热证、脾虚湿盛证等[26]。在中医肾病学领域, 以丁维俊等所做研究为代表[24,27], 其分别选择了成都地区2个遗传背景与生活状况较为一致肾阳虚家系中的肾阳虚证患者 (cDz家系, 11例;Pxc家系, 5例) 为研究对象, 观察其唾液和肠道菌群在种类、数量等方面的规律性差异, 并均发现, 菌群的失调程度与证候的严重程度正相关。在肠道菌群的研究中, 发现两个肾阳虚家系的肠道需氧菌、过路菌显著增加, 这通常是机体对食物腐熟运化功能低下的表现之一;同时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关键性的肠道厌氧性益生菌数量明显减少;且需氧菌与厌氧菌总数之比值在肾阳虚家族之中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其菌群特点不仅可与中医肾阳虚之久泻/五更泄泻/完谷不化等症状相对应, 更阐释了具有相同证候患者共通的生物学基础。而病证结合模型是现阶段中医证候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可以不同疾病同一证候下肠道微生态的变化规律为突破口, 为“异病同治”找到实验依据[23]。
3.中药起效的靶点和作用机制
中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系统调节等作用特点, 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均已证实中药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 是理想的肠道微生态调节剂。正如前所述, 微生态失衡不仅与疾病发病机制息息相关, 更是药物干预起效、改善疾病的“桥梁”和“中间站”。怎样从肠道微生态的角度理解中药起效的靶点和作用机制?又如何对中医肾病学的治疗有所启发?
3.1中草药能够改变肠道菌的组成
许多实验与临床研究均证明此点——例如中草药可以减轻、甚至治疗代谢疾病 (肥胖、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癌症、慢性肾脏病、阿尔茨海默氏病等。基于目前的研究发现, 中草药主要通过协同、拮抗这两种途经发挥作用[28]。如多糖可以促进益生元生长, 进而调节肠道菌群, 促进平衡, 表现为协同作用;通过酶之间的竞争、降低肠道菌代谢能力, 表现为拮抗作用。极性化合物广泛存在于中草药提取液中, 通过肠道菌群的作用后, 其化学成分发生氧化、还原等化学反应, 可以提高口服的生物利用度。
有报道, 一些单味中药、中药复方及中药提取物 (大黄素等) 在由口服或肠道给药后,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保护肠道上皮屏障, 减轻尿毒素蓄积, 调节肠道细菌[29,30], 延缓CKD进展等类似的作用。有研究[31]评价了予CKD5期非透析期患者应用中药复方制剂 (大黄、蒲公英、牡蛎) 灌肠对肠道菌群和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 结果显示治疗组经灌肠治疗后较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同期需氧菌如大肠杆菌落计数等明显减少, 厌氧菌如双歧杆菌、乳杆菌菌落计数明显增加, 且肠道屏障功能的改善, 表现为灌肠治疗组的D-乳酸和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
3.2药物可作用于“肾-肠轴”而起效
有学者认为, 经实验所证实的大黄类经方——“大黄甘草汤”即日本汉方制剂大黄甘草汤 (浓缩颗粒TJ4) 不仅使肾功能衰竭模型鼠的肾功能指标得到明显改善, 而且使得失调的肠道菌群、受损的肠道屏障和免疫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改善其体内尿毒素蓄积的靶点可能是肠道菌群所启动的“肠-肾轴”[29,32], 其机制可能与干预中、晚期CKD患者肠组织中肠道菌群相关的病理因素 (紧密连接蛋白、辅助性和调节性T细胞等) 相关。
3.3重视中药的次生代谢
肠道微生物能够调节宿主对不同类型的疾病和药物做出响应, 但机制并不清楚。其中Steed A L等[33]发现专性厌氧的梭状菌降解植物黄酮类物质所产生的脱氨基酪氨酸对流感病毒感染有利。从中医“脾肾观”, 中医药与肠道菌群、含黄酮类活性成分 (多存在于补益脾肾、补益类) 的中草药[34]与梭状芽孢杆菌 (Clostridium orbiscindens) 次生代谢将是研究的热点。
4.对中医治法的新认识
4.1重新理解中医传统外治法
如前所述, 作为通往“已知”的桥梁, 以肠道微生态为契机和中介, 中医传统外治法的起效机制和路径也得到了更新认识。正如既往研究表明, 而捏脊疗法对小儿外感发热的治疗作用及电针大鼠的“天枢”“足三里”“上巨虚”穴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均可能通过肠道菌群结构而起效[35,36,37]。
回望中医外治法治肾, 张子和认为汗法“开玄府而逐邪气”, 汗法应用于临床治疗CRF自古即有, 然机制不明。有研究的前期实验中发现麻黄汤干预治疗后, 收集大鼠汗液检测并未发现有肌酐排泄增加, 但大鼠血肌酐较麻黄汤治疗前有所降低。后续进一步研究汗法调节肠道微生态与治疗慢性肾脏病间的关系[38], 发现:麻黄汤之汗法能够同时改善CKD大鼠的肾脏和肠黏膜屏障结构及功能, 且与改善大鼠肠道免疫, 减轻系统炎性反应有关。
中医学“浊毒内蕴”是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之一;诸多研究及荟萃分析表明以大黄为主的中药复方灌肠可一定程度上延缓CRF进展, 在清除尿毒素、改善症状等方面有一定获益[21,36]。亦有研究验证[39]:健脾益肾、通腑泄浊法治疗CKD5期的临床及实验疗效均有效, 可调节患者以及肾衰大鼠肠道菌群、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下调代谢性尤其肠源性毒素水平, 从而改善肾功能, 延缓肾功能衰竭进展。正如学者所认识到的中药外治的“双微调平衡”机制[40], 中药外治一方面可调节机体“微生态”即局部菌群生态平衡、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调节机体“微环境”来达到治疗效果。
4.2中医药治疗肾脏病的再出发
肠道微生态为新药研发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药研发必须开始关注人体和共生微生物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人菌平衡”, 并且深入掌握药物对人体共生微生态的影响和相关性[41]。同时也有新问题——中医治疗肾病的再出发:只有药, 才是“药”吗?
粪菌移植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 即将捐赠者或自体肠道功能菌群分离后移植到患者肠道内, 其被视作重建肠道菌群治疗相关疾病的最有效手段[42], 已用于复发性难辨梭状芽孢杆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 感染根除治疗和难治性炎性肠病以及肠易激综合征、顽固性便秘等多种菌群相关性疾病的治疗和探索性研究, 并被认为是近年的突破性医学进展[43,44]。追溯FMT发展历史, 早在东晋 (317~420年) 时期, 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已记载用新鲜的粪汁或发酵的粪水治病:“饮粪汁一升, 即活”[45]。2012年, 我国学者张发明发表文章《Should We Standardize the 1700-Year-Old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46], 将FMT雏形应用于临床的治疗史推演至1 700年前, 并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承认。FMT的良好临床疗效及对不同疾病的治疗潜力, 不仅从根本上引发了科学家从肠道微生态角度寻求多种疾病的诊疗突破, 而且重塑了微生态学作为新学科存在的价值基础。结合新近得到重视的“肾-肠轴”疾病机制,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肾脏病治疗领域, 在肾病-CRF这一关键疾病阶段, 探求如何将FMT整合入调节肠道菌群并从而干预CRF进展的治疗体系具有光明的前景。
小结
重视、理解人体微生态尤其是肠道微生态这座桥梁, 对于健康和疾病, 我们才能看清来路, 也知晓去路。其对于中医肾病学科的意义, 不单单是明确经由何而起效 (机制) 、潜在的中药治疗目标 (靶点) 或开辟新战场, 而是在“微生态”的意义和作用被确立的大时代背景下, 颠覆既往对疾病、健康、药物、人体的传统观念, 开启中医肾病临床证候、治法、药物的新认识, 藉由宏基因组、生物样本库、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浪潮引发的研究, 从量变到质变, 创造机会, 科学发展自身, 从古老传统中焕发新生机。
从“人菌共治”的角度看待中医药, 从调整改善肾病患者肠道菌群以治疗、改善肾病并延缓CRF进展这一视角探寻有效的干预途径、治疗方法, 找到精确、有效的中医药切入点, 探索其作用的分子机制, 建立标准化的微生态研究方法, 为转化医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并向菌群之间、菌群与人体相互作用等更高维度发展, “异病同治”, 开发中医药背景的肠道微生态调节剂靶向调节疾病, 未来终可期。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裴明 杨洪涛
|